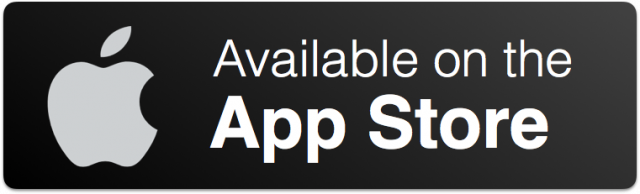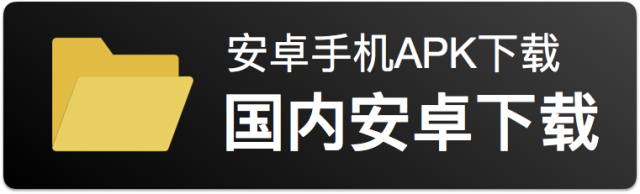清华“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记住也是一种不放弃的态度(美中報道)
今天中午,@清华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我校1992级校友、勇敢坚强的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
2013年,《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个有关“朱令案”的封面报道。报道的契机是因为当时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寝室投毒案,一位医学院的研究生在寝室饮水机里放入剧毒化学品,毒杀了自己的室友。但社会对这起高学历精英投毒案的关注,很快过渡到另一个案子:清华大学的“朱令”案。
“朱令”案发生在1994年。从她在清华就读时出现中毒症状到最终确诊,历时近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朱令的身体被铊毒素侵害,直至陷入昏迷,但负责诊治的医院没能及时确定病因。她的高中同学贝志诚和朋友将朱令的症状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医学界求助,收到一千多封回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
这是“朱令”案中非常让人激动,也是案件长久引起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它在残忍和黑暗中有奇迹,有温暖。但这些温暖没能改变故事的悲剧走向。由于铊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太长,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严重损害。即便后来苏醒,也丧失了绝大部分记忆和生活自理能力,直到2023年12月22日去世。投毒者至今尚未归案。
“朱令”案的封面报道推出后,我们收到了关注“朱令”案志愿者的感谢信,感谢我们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实际上,我们的报道并不能在案件事实上有什么推进。但每个事件都是一个生命体。能够长久被记忆,被持续关注和讲述的事件,就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强的生命体,比如“朱令”案。每一次对它的记录,既是对事件生长到什么状态的了解,也是一种绝不放弃的态度。这种态度能帮我们度过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将事件这个生命体导向不一样的未来。就像《三联生活周刊》最早报道朱令案的记者巫昂所说:“有时候,记忆是某种更为有效的反抗,某种等待时机的态度,以及高于同情的坚韧不拔。”
记者|陈晓刘敏
喧闹
朱令的家位于一个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小区,楼道内光线昏暗,房间的门牌号被各种遮盖物遮蔽着,在楼道转了好几圈,才在一个门上用毛笔写着门牌号的地方找到了她的家。客厅里正播放着“东方时空”2007年的纪录片《朱令的12年》,这是CCTV的一个团队历经一年多拍摄的朱令中毒后到2007年间的生活情况。父亲吴承之坐在沙发上,握着遥控器。当影片出现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他就按下暂停,对围坐在周围的七八个记者讲解几句。他穿一件干净的红格子衬衣,虽然已经73岁,却没有衰老之态,谈吐思维都很清晰。
不停有人进出,每有陌生人进入房间落座,吴承之就微倾上身和气地问:“你是哪里的?”从1995年小女儿朱令被铊投毒并导致生活能力丧失,但真凶至今尚未抓获开始,这个家庭就对陌生人不再陌生了。十几年来,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来到这里,记者、志愿者,希望记录他们生活的人……这个家庭的故事总会因各种契机被不断提起。这一次是因为2013年4月复旦大学的一桩寝室投毒案,朱令的铊中毒悬案再次成为网络公共空间的热议话题。
纪录片播完后,记者们又开始围绕案情提问。这起悬案里有太多追问多年却始终没有确切答案的疑问,迄今没有任何一种讲述能穷尽其中的疑点。吴承之像突然下定决心一样,拍了拍沙发扶手说:“我再给你们讲一遍吧。中毒那段就不说了,从调查开始讲。”于是,1995年前的一幕又重头说起。
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何清是“帮助朱令”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她告诉本刊记者,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致力于筹款帮助朱令和其他铊中毒患者。这些年捐款额起起伏伏并不稳定,最少的一年只有不到15笔捐款。“捐款额有很大变化的时候,一般都有事件发生。”何清说。在此之前的一次捐款高潮是2011年,美国新泽西州发生了一起旅美华人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是北大毕业的妻子,涉嫌用放射性金属铊毒杀了清华毕业的丈夫。
2013年4月复旦大学的投毒案发以来,随着网络交付工具和舆论平台的发达,“帮助朱令”基金会获得了创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捐款热潮。“4月以前,整个捐款是5万多美元。仅仅4月,捐款就达到近5万美元。现在已经到了13万美元。”何清对本刊记者说。以往基金会给每一个捐款人回复一封E-mail,感谢他们的帮助。根据捐款人的不同,在每封邮件填上捐款人的名字。但现在大量的捐款量让何清和同事们不得不省略了这个程序。“每天都有约200封E-mail要发送,只能群发统一的感谢回函。”突然增大的群发邮件量,让何清发出的邮件甚至被一些系统认定为是垃圾邮件,她的邮箱一度不能使用。
除了捐款额大增,每次朱令案再起热潮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民间追凶的热情。朱令被警方确定为被投毒,但凶手至今没有抓获。网友们的大部分愤怒和攻击集中于朱令的一位大学室友——她曾经在案件调查阶段接受警方问讯,甚至有传闻称她是警方确定的“唯一嫌疑人”,在其后十几年里,这位大学室友成为民间追凶的对象。网上有大量认定她就是凶手的文本分析,证据推理以及讨檄文章。而“白宫请愿”更让这桩旧案成为一个国际事件。采访过程中,不时有国外媒体的约访电话打进来。吴承之都婉言谢绝:“我们先在内部解决好。”他对话筒那边说。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作为老一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朱令的父母谨守着内外有别、照章办事的准则。他们拒绝了所有外媒的采访,并在沙发边的一台器械扶手上摆了一个小本子,用来登记国内每位到访记者的单位和姓名。这台器械是吴承之自己组合,本用来训练朱令的站立。但在一年多以前,朱令因为一次小感冒导致肺部感染,气管被切开,身体比以前更为虚弱。她已经很久不能做站立练习,器械上堆满了杂物,还有一束探望者几天前送来的百合花,昏暗窄小的房间里有淡淡花香。
朱令父母目前最大的愿望,除了朱令能自主生活外,就是要求朱令案信息公开。根据这十几年来累积的各种消息,他们相信“一旦这个案件的信息公开了,真相也就知道了”。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他们就开始申请朱令案信息公开。“我们抢到了申请市公安局信息公开的第二号。”吴承之回忆,“但市公安局以该案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况’,回复了一封不予公开的告知书。我们当然不服了,根据法规,我们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就一次次地开始复议,一直折腾到2009年3月16日,最后北京市政府有一个行政复议决定书,推翻了原来的布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于2005年5月30日做出的2008年第2号布告‘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是一段类似访民的艰难经历,吴承之手里累积了一摞申请该案信息公开的政府回函。2009年的政府回函看起来给朱令案信息公开一线生机,但撤销市公安局的布告后,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案。信息公开一事又石沉大海约4年。这次因上海复旦大学的黄洋中毒案而引发的新一轮对朱令案的关注和讨论后,“平安北京”于2013年5月8日发布了《北京警方回应朱令令案》的公告。警方声明发出的第二天,朱令家立刻聘请了律师,再次起草了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书。文章措辞平静,秉承着朱令家的一贯态度——不激烈,也不放弃。吴承之对记者出示这份声明后,有一个记者再次让他发表对“平安北京”声明的看法。“我刚才说这么多还没听明白吗?你还要我表什么态呢?要我喊口号吗?”这位一直平静温文的老人有点生气地举起了拳头。
这是吴承之在面对媒体的两个多小时里,唯一一次情绪有点激动。其他时间,他都耐心应对着各种琐碎又熟悉的问题,嘴角常常挂着无奈的微笑。实际上,关于案情本身,经过10多年时间的冲刷,民间的各种情感为案件掺杂了许多真假难辨的信息,看起来案件的信息是越来越丰富,但案件可讨论的确实起点却越来越模糊。要求办案部门信息公开可能是最大限度逼近真相的唯一途径。
接待采访的时间在下午15点到17点之间。这是朱令休息的时候,朱令父母才可能有精力面对媒体。5月9日这天下午,正规约好的媒体就有4家,还有前几日采访过但希望能得到更多信息的记者又登门。吴承之有些无奈地笑着挥手对他说:“你就回去吧,同样的话你都听3次了。”少见的络绎人流,还引来了警察的关注。这天一共有6个警察分次来到朱令家中,查看到访者的证件。这是朱令案起起落落十几年,第一次有警察到家中造访。
情感
2013年5月,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出现了6个演唱版本的《大麦歌》。这是美国现代女诗人沙拉·迪斯德尔的一首诗Like Barley Bending,网上谱曲的版本是该诗的中文古诗体,有传言是朱令高中时的译作。但随后有网友指出,这首被传唱的《大麦歌》与李敖1960年的译作极其相似,而且很可能并非出自朱令之手。朱令母亲朱明新也告诉本刊记者,她从未见过朱令翻译这首诗,“看到央视新闻上播出朱令翻译的《大麦歌》,我还觉得很奇怪呢”。
但这事符合民间对朱令案的情感记忆:被伤害的是一个非常优秀、具备充沛情感和生命之美的女孩。因情感造成的信息扭曲很容易被人原谅和忽略。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在微博中写到:“无论如何,这首诗献给朱令还是很合适的。”诗歌的最后四句——“我生亦柔弱,日夜逝如此。直把千古愁,化做临风曲”——被网友们认为是朱令让人叹息的命运写照。
为了朱令通过互联网向国外求助的贝志诚
王晓丽和朱令是小学同学。“我们都在崇文区的光明小学,这是所挺不错的小学。朱令是那种老师特喜欢的学生,聪明早慧。她学习成绩特别好。我记得小学时候参加手工制作的展览,我们做一些小手工、航模,觉得都挺正常的,朱令就做了一个日晷,就是古代的计时器。一个小学生能有这个创意,很有智慧。她是一个很自律的孩子,不需要别人监管她,自发地学习。老师一说起她都很怜惜,都是让她‘休息会儿吧,去玩一会儿吧’的样子。”王晓丽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们老一块玩,他们家就住在光明小学围墙外面,有时放学后我就去他们家玩,捡来树叶子搁在锅里煮煮,再用牙刷拍拍拍,把叶肉敲掉,叶脉留下,夹在本子里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书签。”
朱令的姐姐吴今也是学校里的佼佼者,“是需要仰视的人物。我们玩的时候,能看见她姐姐的照片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楼道里挂着。她们姐妹俩小学、中学、高中都是一路保送的”。王晓丽回忆说。

儿时的朱令
姐姐吴今曾经是崇文区的理科状元,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上北大生物系。一位因拍摄纪录片跟朱令家很熟悉的记录者告诉本刊记者:“吴今从小跟姥姥姥爷学外语,在80年代就能跟外国人对答如流。在那个年代她就学习芭蕾舞、弹钢琴。”网上还能找到一张吴今的照片,是黑白摄影,更显得那个年代不矫揉造作的朴素美感,有网友评论“真的很像山口百惠”。
1989年吴今在学校组织的野三坡游玩中,不幸坠崖身亡。姐姐的逝去给朱令的打击很大。初中同学贝志诚回忆,那段时间朱令不那么活泼了,变得有些孤僻。甚至后来报考大学时,她舍北大报清华。“本来也想考北大,因为她姐姐在北大出的事,她感情上受不了,所以去了清华,所以,人生轨迹也是这些机缘巧合。”吴承之对本刊记者感叹。
在朱令被投毒前,她的成长很少让父母操心。“她自己都安排好了。家长会我去什么事都没有,成绩一公布,她差不多都是前几名。开完会就走,老师也不会点名让我留下来。当时学古琴也是她自己觉得好听要求学的,我们只是打听到哪里卖古琴,哪里有老师教,就去学了。她的钢琴和古琴老师我都不认识。”吴承之对本刊记者说,“朱令从高一开始学古琴,一直学到大学。最后老师也不收她的课时费,一学就一下午,后来两个人就变成切磋了。这次生病后,他的古琴老师还来到家里,带了一张明朝的古琴,给朱令弹了两个小时,声音真是好听。”
朱令家庭的故事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在于,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遭遇不幸,而且是两个特别热爱生命、有能力探索生命、展现生命之美的人遭遇不幸。“朱令是先弹钢琴,后弹古琴,弹钢琴不能留指甲,古琴要留指甲,她就要算,这一周今天弹钢琴,几天能留出来指甲弹古琴,还要算出时间保留体力去游泳。朱令‘大二’还在学德语,她当年想去德国留学,因为德国的化学工程是全世界最好的。甚至在她神经系统被毒素摧毁之后,学过的德语还零碎停留在她的记忆里。有时候问她,她还知道一些。”一位曾长期为她拍摄纪录片的记录者张瑾对本刊记者说。
朱令
每隔一段时间,她的故事被以各种方式流传。除了假托《大麦歌》的译作外,还有以朱令中毒事件为原型的小说《未名花殇》《蓝色的泪滴》等。人们希望以各种形式记住它。张瑾从2006年开始走近这个家庭。她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的想法不是迅速地做出来,完成一部作品,我是想留存一个资料。叔叔阿姨今天打电话告诉我,前几天柴静、董倩也去过了。不管是否能播出来,她们说咱们先留个资料吧。这是我们都达成的共识。”
除了美和痛,这个故事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还在于案件有无数吊诡之处。朱令被投毒,凶手至今不明。有相当多的人,包括她的至亲和好友相信凶手已有确证,但因为家庭的显赫背景而干扰了司法,从而逃脱制裁。何清对本刊记者说,她也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比朱令稍长一点,就读于北大。“看了朱令宿舍的位置图,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她小时候的照片,就想到我小时候在北海照的照片。我的父母也和她父母一样是知识分子,我感觉我们很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差不多的家庭、生长环境。对她的不公平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不公平。”
追凶
何清说她第一次知道朱令中毒事件,是1996年通过一本美国的畅销读物《读者文摘》。“一位美国同事给我看这篇文章,说这是你们中国的事情,这个故事真的很特别。”这篇名为“Rescue On Internet”的文章,讲述了朱令的初中同学贝志诚就朱令的病情通过互联网发出求助信后,收到世界各地医生的回复和帮助,并最终确定朱令中毒源的故事。
1995年,朱令案发时,因为学校和警方的消息屏蔽,这个案件当时并没有在国内大范围传播。但通过互联网却在美国持续发酵。何清记得后来美国Fox News也报道了此事,并提出了这是一起投毒案,发出了“凶手是谁?”的疑问。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国外媒体早期提到这个案子的嫌疑人时,将其描述为“求爱不遂者”,而非今天网上盛传的室友嫉妒投毒。
当何清再次了解这件事,是在2005年“天涯论坛”上,距离朱令中毒案发已有10年。天涯网上出现一篇题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帖子,重述了朱令案,并提出了当时的嫌疑人孙维。“我很吃惊,当时不是说醒了吗,没想到残疾成这样。而且凶手没抓着,还来了美国。这事太过分了。”
2005年,朱令案是重新大范围进入民间视野的一个事件。继“天妒红颜”发帖重提朱令案极其嫌疑人之后,孙维也在天涯网上发出了自己的声明,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对朱令的家人和一些朋友来说,这封自辩声明反而提供了一系列孙维就是真凶的证据。为了敦促破案,朱令家1997年的3月25日给北京市公安局时任局长张良基写了封信。大致内容是同学要毕业了,这个案子如果不破,大家都走了就没法破了,希望他抓紧破案。5月20日给中央领导写了封信。“写完信以后也没什么结果,中间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吴承之对本刊记者回忆,“但2005年‘孙维的声明’里也讲过这个信的事情,她写道‘关于所谓领导人和公安对我的包庇,网上义愤填膺,事实是公安从来未对我做出任何包庇,朱令1994年中毒,1995年确认,到1997年一直没有破案,应该说错过了破案的最好时机,眼看大家要各奔东西,朱令家人非常着急,后来我得知,1997年3月25日,朱令家属致信公安局长……1997年5月上书国家领导人。’我们确实给中央写信了,但孙维知道具体的年月日和写信的内容,这说明什么问题?以前我可能只是有点怀疑,她们同学之间怎么能仇恨那么大,那么自私,但我看到她的声明之后,我就认定了,孙维是唯一的,就是她干的。”
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约2006年,朱令家聘请了律师张捷和李海霞。“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引导网上舆论,并收集新的证据,为以后的重启调查做准备。”李海霞对本刊记者说。朱令吧是民间追凶热心人士的主要阵地。何清还记得,当时有个网友“隔世追铊”写过一篇文章:《和孙维促膝长谈》,“写得特别美,文字表达很好”。
除了情感上的表达,网友们还自发追凶,四处联络当时的同学,搜集证据。何清也曾积极参与。她记得当时主导追凶的一个负责人是学犯罪心理学的,家庭也有法官的背景。大约在2007年,何清趁去日本出差的机会,受这位女士之托,去爱媛大学找了朱令的清华室友金亚。“开会完了,我留了两天时间,去了金亚的学校,找到她的实验室。看见一个小个子女孩出来,刚好就是金亚。她对我们的来访并不是很乐意,但还是和我们去附近一个咖啡馆聊了一会。”金亚给何清留下的印象是haunted,“这是一个中文很难表述的词,我感觉她心中有阴影”。
谈话是在何清保证“客观”,并表示不会将谈话内容发表到网络BBS上后进行的。“金亚说,你在网络上说任何话,人们会按他们所想要的方式去解释。”当谈论到案子时,金亚说,这件案子非常复杂,牵扯到很多人,公安都没有结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凶手呢?“我对金亚说,这件案子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并不复杂。金亚说,那是你只看到一个分支,但这件事情有很多条分支。她用手指在桌上画了棵树的形状。她说,朱令有很多活动,而且寝室相处很好。当朱令说肚子痛的时候,她们把朱令送到校医院,并嘱咐舍监给朱令留门。”
何清对谈话中的两点印象深刻。“铊中毒非常疼,朱令最后的疼痛,连被子盖到脚背都难以忍受。但金亚说,她没有印象听到朱令喊疼。朱令心气很高,可能疼也自己忍了。”何清告诉金亚,在《朱令12年的纪录片》里,朱令在医院因为疼痛抓着床沿尖声大叫。“我能感觉她听到这话后心跳加速,并避开我的眼神。后来金亚说,公安有我们所有的问题记录。我们在每页上都有签名。当有人再来问我这案件时,我告诉他们,去跟公安谈。如果公安要重审这个案件,我很乐意自己买机票飞回北京协助调查。”
和金亚见面后,何清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并交给了朱令父母。后来何清帮助朱令的重点渐渐转向基金会,因为感觉,“追凶更大程度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并不是我们的特长,还不如做一些更实在的帮助。比如给她筹款,带一些康复训练的器械。但很多追凶的网友仍在继续。正义不到朱令家,我们会把正义送过去”。
信息旋涡
2005年底,为千夫所指的孙维为什么要发表自辩声明,两方有不同的解释。认定她是凶手一方的解释是,她多年希望出国,但一直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未能成行,她希望洗白自己。而孙维及其家人的陈述却是,他们多年来受到舆论审判,自己及家庭已不堪困扰,决定出来澄清。
我们不能判断哪个原因才是事实,但孙维这些年确实很不好过。用何清的话说:“如果她是凶手,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受到的惩罚一点也不轻。”她一度想出国,但申请一直没有被接受。“帮助朱令”基金会中有一位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医生,也曾参与帮助朱令找到病源毒物。他透露孙维向大使馆申请赴美,但因为朱令案,申请没有成功。此后她辗转做了多次出境的努力。“2005年以前,我也接到过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对方说孙维在广州,申请去美国,问朱令投毒案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意思一听就明白了,各地都堵她。”吴承之对本刊记者说。
2005年底到2006年,是朱令案“谁是凶手”在网络上掀起的一次高潮,也是目前所知的孙维及其家庭唯一一次想要说点什么的时机。孙维的母亲两次致电朱令家,希望能和他们谈谈。朱令的父亲向本刊记者证实了这个事实。“她当时就是想要我们帮她澄清。但通过孙维的声明,我们认定就是她,不会理会这样的要求。”
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2006年,朱令案的讨论在天涯网上分外喧嚣之时,孙维和家人答应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的邀约。一位当时负责筹备这期节目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她联系天涯网上发表孙维声明的ID,大约一天后就收到对方的回应,称愿意接受谈话邀约,但需要栏目组支持的态度。“其出发点很明确:我要证明清白,必须是为我证明清白。”这位工作人员回忆说。
这个ID的管理人是孙维的哥哥。投毒案后,朱令的家庭得到大量舆论的同情和安慰,这个家庭则收到大量的恐吓和辱骂。不管警方的陈词和结论如何,案件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凤凰卫视的一位工作人员记得,第一次与孙维方见面是约在一家咖啡馆,只有孙维的哥哥出面。“他看起来像一个整洁的、有素质的人,但很疲惫。他诉说了家庭在孙维被公布是朱令案的唯一嫌疑人之后,很受困扰,几乎无法继续生活,即便搬家、换电话仍然不断被骚扰。半夜被打电话、家里半夜被塞进信,但他们也选择承受。”不管是否有罪,孙维也在尽力试图修复自己的生活。“孙维的哥哥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诺基亚,并主导研发了诺基亚的一款用智能笔书写的手机。”一位当时曾与孙维哥哥多次联络的凤凰卫视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们最初的节目设想是让他们和朱令家两边对话。孙维的哥哥表示可以接受测谎仪,并要求栏目组保证公正的立场。但随后又说‘(公正的立场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们”指的是网络上认定孙维是凶手的舆论力量。在孙维要上“鲁豫有约”这档节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我收到大量电邮、电话、短信,持续不断,告诉我孙维就是凶手。你会感到一种很强的诉求扑面而来。这股力量是很吓人的”。一位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孙维哥哥和栏目组进行多次前期接触后,孙维在人民大学附近的“鲁豫有约”办公室和节目组见了一面。两位参加过当时见面的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孙维,第一印象都是“瘦小”,跟网络上贴出的微胖照片很不一样。“她身穿灰白色上衣,深色裤子,没有化妆,跟着哥哥进来,感觉非常瘦小。以至于我怀疑网络上她的照片是不是真的。”
在这次约3个小时的见面里,孙维是最主要的讲述者。她要表达的和她哥哥之前表达过的如出一辙——她以及家庭受到的打扰和冤屈。“她气场很强。讲述时语速很快,也很平静。我记得她说,很多人打电话去她爸爸的办公室,以至于她爸爸为了躲避铃声躲到椅子下面。她自己也有几次试图自杀。有一次因公出差到了一个海边,她就想跳海死了。她用了很多书面语,很详细地描述了海滩的氛围,她如何在海边徘徊。”一位参与过见面的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见面结束时,他们交给主持人陈鲁豫一封约有十来页的长信,说是孙维妈妈写的,希望她能好好看看,给他们一个支持的态度。
但节目最后还是没有实现。在听孙维和家人的陈述时,一位当时参与节目的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我当时有点后悔了,觉得之前大量涌入的电邮、短信,让自己陷入一个巨大的信息旋涡。旋涡一定是有方向的,牵扯着往下走。如果你之前有判断,那方向一定就是她是凶手。”
节目的夭折,或许已经说明,对一桩发生在好几年前的悬案,缺乏只有公权力才掌握的事发当时最确凿、最准确的信息,民间很难有能力完成对这个案件的质疑和对话。而当时的取证机构在信息公开上的沉默,只能让民间的信息旋涡越来越大,争议双方已不存在一个可交流的对话空间了。
尊严
对大多数第一次到朱令家拜访的人来说,进入这个家庭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贝志诚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觉得心理上难以承受,他很少去朱令家。“我特别能理解贝志诚的想法。”一位曾跟踪拍摄朱令两年,并至今保持联系的记录者对本刊记者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家接触都是若即若离的,我有贝志诚那种感觉,第一你爱莫能助,第二这个家庭还是给人一种非常非常深的沉重感。”
毒素在十几年前摧毁了朱令的神经系统。“我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她已经不是朱令了,完全是另一个人,我认为‘她’不能代表朱令,这就是一个残留了一些朱令的灵魂的一个人。”王晓丽对本刊记者说。

《朱令的12年》纪录片
朱令残留了一些她以前的智慧,能让人感觉到她灵光一现的地方。她经常听新闻,听音乐。“有一次我在他们家的时候,听到有人弹古琴,朱令立刻就说,他弹得不好,意境不够。就寥寥几句,就能知道这个女孩对艺术是有造诣的。”张瑾对本刊记者说,“有时朱令会发脾气,但是只要听到古琴深沉的琴声,立刻就安静下来。但是叔叔阿姨很少给她听钢琴,据说有一次,朱令听着一首钢琴曲,突然悲痛不已,叔叔说,那时她突然想到了姐姐。”
但她的状态很不稳定。她有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偶尔也会跟父母大发脾气。“她经常回到大学时代,突然觉得该去实验室做实验了。她爸站在轮椅前头要给她处理什么,她就非常生气,大叫:‘你让开!别拦着我!’”王晓丽说。
王晓丽曾经想过利用儿时伙伴的远期记忆去刺激她。“朱令是有远期记忆的,小学、中学的事情她还记得,大学只记得一部分,最近18年就是空白的。几年以前她的父母和我对朱令还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出现奇迹,我也挺热血沸腾、挺理想主义的,觉得做这个治疗、那个刺激,怎么能进入她的内心世界。我还找了教英文的朋友,想从语言上刺激。我幻想过好多她好起来的场景,现在想起来,还是想得太美好,实际上她的脑子已经被摧毁得不可逆了。现在我明白了,根本不行。”
“我感觉她这几年的状态确实是往下走。”王晓丽告诉本刊记者,“最主要的是脏器功能在衰竭。有一次就因为一个小感冒,低烧,正常人多喝水,睡一觉就好了,但她的身体就像一个满是裂纹的杯子,大夫怕呼吸不上来,就直接给切开了,报病危,在医院住了一年。我们的心肺在走路、坐着的时候有正常的运动,但朱令相当于一个静止的状态,心肺怎么可能正常?她呼吸跟我们不一样,肺功能在逐步萎缩,晚上要吸氧,要定时吸痰。小脑萎缩之后,她的平衡功能、吞咽、控制口水的能力都不行了。以前她还有吃的乐趣,但气管切开后,食物都要打碎了给她,连这点乐趣都没有了。”
“我觉得朱令活的每一天都是她的父母为她注入生命。她的父母24小时看护她,不可能真的安枕无忧地睡觉,因为万一氧气没戴好,或者有痰卡住了,可能因为一口痰就出意外了。她父母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也没吃过正常的饭。朱令躺在床上吃了之后也不消化,她爸爸就根据她的体质调中药,泡完之后做足底的点穴按摩。”
这个家庭有着抹不去的沉重底色,但朱令的父母把这种悲伤很体面地隐藏着。对所有提供帮助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流露过很强烈的悲伤情绪,父亲甚至时时表现出一点幽默感。“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大家看电视,朱令在器械上练站立,他就拿了张报纸卷起来说:‘朱令这是火炬,举着!’”张瑾对本刊记者说。
朱令的父亲正在帮助朱令做康复治疗。朱令完全依靠父母照顾,让朱令能够生活自理始终是这对老人的期盼。
虽然住的房子仅有100平方米,被分为四室一厅,但每个房间都小而整洁。墙上还能看到淡色的墙纸,绿白格子的地板也很干净。来访的客人多了,换的拖鞋不够,吴承之会给每人一个塑料袋套在脚上。张瑾还记得:“有一次拍朱令做康复时,朱令一下子把吴叔叔的衣服肩部拉裂了,叔叔就立刻说,这个别拍别拍。叔叔不是怕自己出丑,更主要是要抱有尊严和体面。”
在拍摄纪录片期间,朱明新曾经跟张瑾讲过两件事:“朱令当年在宣武医院住院,有个康复大夫想用朱令做一个教材,讲如何让病人站起来,阿姨虽然不想让人拍这样的朱令,但她也想,朱令已经成这样了,还能为人类,为康复事业做点事,她愿意,相信朱令也愿意的。汶川地震,阿姨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她想告诉大家,朱令还活着,有情感、有尊严地活着。”
最近几年,王晓丽坚持去朱令家探望他们。“我们从过去的朋友变成像现在像家人一样的关系,我看到她家有他们自己的天伦之乐,因为他们家现在是一个铁三角一样的家庭关系,朱令跟她父母非常心有灵犀。我记得几年前,那时朱令的状况比现在要好。有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跟吴叔叔谈话,朱令就生气了,吃醋了,捅她爸爸:‘你,到,底,是,谁,的,爸爸?你,是,我,的,爸爸!’他爸爸听到她有这个情感的诉求,也很高兴。”
“我现在不觉得难过。”王晓丽说,“就觉得拿她当一个小孩,一个比较庞大的小孩。气管切开前,她对吃很感兴趣,喜欢吃橙子,就会摸她爸胳膊一下,意思是她想吃橙子,甜的。朱令特别听话、特乖,让她做什么她都很努力地去完成,她爸给她泡脚的时候,她就双手上下举一根棍子锻炼上肢……其实很艰难,她没什么平衡能力,控制不了自己。但她还是很努力地练习。”
张瑾说朱令的父母,“在痛苦面前保留了人类的尊严,有一种最大的忍耐,对体面的追求”。虽然家里发生过悲剧,但他们没有让自己的生活也成为悲剧,甚至还能给探访者温暖。王晓丽说:“有时候我有烦恼,吴叔叔就介绍他自己的经验,说‘你看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就是悟,要不然我怎么能熬过来呢?’我没问他‘悟’了什么,但我很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在他脑子里一定有很多想法,他一天悟了多少次,一年又悟了多少天呢?”(原创 陈晓刘敏 三联生活周刊)